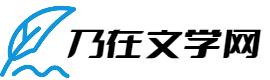宗璞《报秋》阅读答案,宗璞报秋蕴含哲理
北京大学燕南园57号院,是燕南园十七栋房屋中唯一一座中西合璧的建筑,巧合的是一生“融汇中西,贯通古今”的哲学泰斗冯友兰先生就在这里居住,在这个看似平静的青砖灰瓦小院里,冯先生经历了思想改造的风暴,也创造了劫后余生的辉煌。
视频加载中…
冯友兰先生在《三松堂自序》中写道:庭中有三松,抚而盘桓,较渊明犹多其二焉。”“三松”不仅是院中一景,冯先生将其与陶渊明作比,可见他人生跌宕起伏后的心境与寄托。由于哲学和文学的滋养,这个原本普通的院子成了燕园的一个文化符号和哲学象征,时常有人来看望三松堂,在门口拍照留念,曾有一个四川读者在三松堂院子里恭敬地三叩首后离去。
初识哲学
2006年11月的一天,在友人的引荐下我第一次走进三松堂。推开一米多高的木栅栏门,一棵华盖般的松树耸立在庭院中间,临近西边是近年补栽的一大一小两棵松树。三松堂是一座口字型的中式建筑,从正中间一分为二,东边与哲学家汤用彤家为邻,建筑内部北面是客厅,并有走廊连接西、南各个房间。在客厅落座不久,宗璞从卧室走了出来,那时她视力、听力还好,我自报家门后,宗璞简单介绍了父亲的成就,希望父亲的纪录片能拍成功,临走送我一本有她签名的《三松堂自序》,从此开始了我与三松堂的不解之缘。
随后的十几年里,我无数次出入这个庭院,用镜头记录了宗璞口授《野葫芦引》的艰辛过程,见证了宗璞搬离三松堂,以及三松堂从荒芜到翻建的每一次变化。更重要的是对冯友兰先生的哲学思想和治学精神有了更多了解,受用终生。
冯先生出生于1895年,这一年发生了“公车上书”事件,标志着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。生逢“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的时代,冯友兰一生满怀救国理想,与时俱进,是学术“趋新”的代表人物。
冯友兰先生所接受的教育和后来学术思想的总基调就是“新”,早期教育是在新式学校武昌方言学堂,中学教育是在上海中国公学,大学教育是在当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,博士教育是在思想较新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。他后来的哲学思想、研究方法、术语概念以及学术著作的体例创造都是前所未有。
“新儒家”也是冯先生最早提出并继往开来的。百年之前,冯先生那一代学人思考的是如何复兴民族文化,重振古老中国的雄风。面对中西文化优劣的争论,冯友兰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异,其实是时代的差异,把中国古老的文化改造为近代和现代的文化,是完全能够实现的。他把“程朱”以来的“新儒学”又加进了“西”的内容,从而完成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。
晚年的冯友兰又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,写出了150万字的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,把中国哲学推进到一个新高度。他用“三史六书”诠释了“旧邦新命”的辉煌人生。
云在青天
走进古色古香的三松堂,第一印象这里是书的世界,每个房间甚至走廊里都是书柜。沿走廊往南走,尽头左拐正对走廊那个房间原是冯先生的卧室,也摆放着几个装满书的柜子,抽出几本翻看,是韩文、意大利文、法文甚至塞尔维亚文的《中国哲学史》。东墙上悬挂着冯先生手书的“阐旧邦以辅新命,极高明而道中庸”对联。这两句话是冯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。
宗璞在《三松堂断忆》中写道,父亲执着的精神背后有着极飘逸、极空明的另一面,一方面是儒家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的担得起,另一方面是佛、道、禅的“云在青天水在瓶”的放得下。
住在东隔壁58号的汤一介先生在所著书《我们三代人》中回忆,自己曾被拉到三松堂去陪斗,看到已届古稀之年的冯先生被强制站在一把椅子上接受批判,汤一介总担心冯先生会掉下来,然而他看见站在椅子上的冯友兰稳如泰山、面不改色。事后,汤一介问冯先生当时在想什么,冯先生笑说:我当时什么也没想,我在默背慧能的‘菩提本无树、明镜亦非台,原本无一物,何处惹尘埃’。
中国文人一直推崇松的品格,都愿意以松为友,冯先生亦然。晚年他常在三松下散步、静坐沉思或会客,潜移默化中,松之德与三松堂主人们的精神内涵高度融合,达到了浑然一体的境地。
或许是冥冥之中的天人感应,1990年冬,冯友兰去世不久,一场大雪把三松堂最老的一棵松树压垮了。2004年宗璞的夫君、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蔡仲德去世后,松树又枯死了一棵。三松堂的松树,只剩下了一棵,宗璞还守护在这里,完成她的文学使命。
风庐风庐
三松堂不仅是一处哲学圣地,也是一座文学殿堂。宗璞小说的成名作《红豆》在这里诞生。散文《丁香结》《紫藤萝瀑布》,小说《弦上的梦》《三生石》《鲁鲁》,四卷本长篇小说《野葫芦引》等几乎都是在这里写成的,她的作品给几代中国读者带来了心灵慰藉。
作家王蒙曾感叹冯友兰有宗璞这样的女儿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,也有人称赞宗璞为“京城第一大孝女”。宗璞从小到大,工作、结婚几乎没有离开过家。1977年母亲去世后,在宗璞的细心照料下,父亲口授完成了150万字的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。而晚年的宗璞和晚年的父亲如出一辙,宗璞也是在双目几乎失明的情况下,口授完成了四卷本《野葫芦引》的后两部。
宗璞把三松堂称为“风庐”,我曾求教“风庐”的缘由,宗璞说,这栋房屋四面透风,最重要的是自从父亲搬到这里后,一直站在风口浪尖之上,三松堂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,所以叫“风庐”。
然而,风庐文学作品的主题都是追求美好高尚的人生,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认为,宗璞把父亲的哲学思想融入到小说之中,通过文学强化父亲的哲学梦想,父女俩表达着一个相近的主题,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佳话。
一花一木总关情
北大我最爱去的地方是燕南园,这里的每一栋建筑和一花一木都感到亲切,十几年来,我多次用影像记录了燕南园和三松堂的四季变换,这是对文化的敬重。难忘的是2013年3月20日夜,一场罕见的大雪不期而至,银装素裹的三松堂也显出前所未有的圣洁和庄严,恰似人间仙境。这个场景后来成为纪录片《冯友兰》中的经典镜头。
2012年9月9日,宗璞搬离住了六十多年的三松堂,因为这里计划建成冯友兰故居对游人开放。据我所知,宗璞是离开燕南园的最后名人。搬家这天我也过去帮忙,宗璞把三松堂大部分家具、物件和部分手稿捐给了北大,待三松堂修缮后回归原处。书籍大部分捐给了清华大学,捐给唐河冯友兰纪念馆的几件家具、衣物,由我联系物流打包运走。
我知道刚开馆的唐河冯友兰纪念馆缺乏“真品”,于是趁此搜遍三松堂的每一角落,在废弃的地下锅炉房找到两个七十年代的铁壳茶瓶,又在院子东北角的储藏室里发现几个原本准备扔掉的旧木箱,都送给了冯友兰纪念馆。
藏室里还有两箱落满灰尘的黑胶木唱片,都是宗璞听过的外国古典名曲,灌制于上世纪四十年代,很重,总共有一百多斤,清华和北大都不愿意要,经宗璞老师同意,这些唱片由我来收藏,算是三松堂留给我的最好纪念。
经过一天忙碌,物品各有去处,三松堂已成为一座空房。望着宗璞远去的汽车,感觉心里空荡荡的,我知道,以后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随时推门而入,与宗璞老师畅谈了。
哲思永存
三松堂荒芜的5年多时间里,我曾多次去探望、在门口徘徊,眼见满院荒草萋萋、野树疯长,想起唐代诗人崔户的《题都城南庄》,不禁伤感,三松堂院内的花草不知道哲学老人已经仙逝、爱花人宗璞已经搬走,墙边、松下、砖铺小径边的连翘、二月兰、玉簪花仍年年开放,履行着迎春、送春、报秋的职责。
不忍岁岁花开无人问的寂寥景象,2014年5月我把三松堂院内的一簇玉簪花移栽到了唐河冯友兰纪念馆,同时移栽过来的还有几棵铃兰。玉簪花曾多次出现在宗璞散文中,她曾称赞玉簪花有“工作向上比,生活向下比”的良好品质。三松堂翻建后,原来满院的玉簪花现在所剩无几了,而这簇沾满哲学与文学灵气的玉簪花在故乡唐河花繁叶茂,年年绽放,张扬着无穷的生命力。
2018年8月,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在北京召开,在此之前三松堂被修缮一新。因为早在1934年,冯友兰先生就应邀出席在布拉格举办的第八届世界哲学大会,并做了《哲学在现代中国》的学术报告,这是第一次在世界上发出的中国哲学声音。冯先生作为享誉世界的哲学家,瞻仰其故居,是北京哲学大会与会学者们的一个愿望。
同时,我也制作好了中英文字幕的纪录片《三松堂的故事》,准备向来客播放,然而,不知什么原因,后来三松堂“冯友兰故居”陈列布展并未往下进行。
时光如梭,转眼间已是2019年岁末。百年以前的1919年,冯友兰先生抵达大洋彼岸学习西方哲学,自此开启了中西文化比较、融合、创新的先河并卓有建树。“贞下起元”,世纪行过,冯先生“旧邦新命”的学术追求在新时代仍具有重要意义。
我想,无论以后三松堂是否布置成冯友兰故居并不重要,只凭“哲学三史”以及充满家国情怀的《西南联大碑文》,就足以使冯友兰先生穿越时空,永照汗青。(作者许进安系央视大型纪录片《冯友兰》导演)
本文地址:http://www.naizai.cn/archives/11623
以上内容源自互联网,由百科助手整理汇总,其目的在于收集传播生活技巧,行业技能,本网站不对其真实性、可靠性承担任何法律责任,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。特此声明!
题图来自Unsplash,基于CC0协议